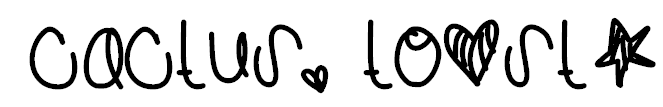《春光乍洩》(1997)由王家衛執導,張國榮及梁朝偉主演,票房達
$8,600,141,在本港及國際影壇屢獲獎項;上映時已有莫大迴響:香港回歸議題、演繹方式、剪接、拍攝手法……事隔十多年的現在,《春》已不單是電影,而提升至值得被學術琢研的層次。這套大方談論同性戀人的「異流」經典,在性與性別的範疇上,卻隱晦地顯現了香港主流傳媒最傳統封閉的思想。
先
不論電影,張國榮本身就是一個性別議題。衣著是界定性別最直觀的表達和感知﹣﹣衣飾的款式、剪裁、顏色,提供了辨識是男是女的第一資訊。張國榮徹徹表現了
「多元性別系統」(Sabrina Petra Ramet: Gender
reversal),將本來二元對立的性別觀念,透過行為退著轉成可越界切換,顛覆了根深蒂固的性別架構系統。香港的媒體是性別抑壓的,男就是男、女就是
女,不容互涉;但張國榮陰柔的第三性穿著使他穿梭於兩極,男女角色隨易裝交替而轉換:兩片紅唇配雙豔紅高跟鞋,唱畢歌曲後又在台上換回男裝皮靴;甚至有時
「雌雄同體」:一頭漂逸長髮又留鬍子。一個知名藝人的表現正面衝擊了大眾約定俗成、對性別疆界分明的普遍認知。
話說回頭,
王家衛多翻強調《春光乍洩》與性和性別無關,只是一個單純彼此相愛的故事,可以套在男男、女女或男女。連飾演何寶榮一角的張國榮也曾說過:「王家衛拍這個
戲聰明的地方,是將一個同性戀的故事拍得與一般異性戀無異,在這方面,他是成功的。」但我疑問,既然這不是一個同性戀的故事,何不乾脆找一個男一個女、或
一是一對女來演呢?這是以同性戀作為綽頭,還是別有用心?若是前者,王的確是成功的。
王家衛又完全刪除關淑怡的戲份,令《春光乍洩》中一個女角色也沒有,是不是因為逃避性別議題,而索性令觀眾沉溺於光影世界,讓觀眾片刻忘懷世間有男女之別?
電
影優勝的地方是,從一開始便是何寶榮和黎耀輝(梁朝偉飾)激烈的性行為、從頭到尾也沒有質疑過性取向這個老生常談的議題。同志戀人終於在螢幕上恢復人性及
性愛的權利,而不是每每將同性戀人的真實性避而遠之,聖人化他們以換得觀眾諒解和接納;反而是擺出同性戀理所當然的姿態,同志就是同志,不必被討論、不必
要解決。
此外,香港主流傳媒喜用易裝反串方式扮演同性戀者,又以過分浮誇的演技恥笑他們半陰不陽;來製造喜劇效果。不過《春光乍洩》中的一對同性戀人外型寫實﹣﹣就是徹徹底底的男人;恐同意識相對低,表面上未見給同志帶來傷害。
然而看深一層,要是問我《春光乍洩》是否一套好的同志電影,我會說這其實片中的角色刻畫、性別意識形態上依舊還是傳統異性戀,埋藏著男女二元觀的刻板模式;這根本不是一套同志電影,仍然活在異性戀霸權的陰霾之下。
主
流的愛情價值觀總是富有性別色彩:男人是得益者,女人是可憐的悲劇受害人。即使戲中的主角是一對同性戀人,他們心理上仍是典型異性戀者,關係中的互動有分
男女、個性鮮明。黎耀輝是「女方」﹣﹣專情、卻被辜負:即使發高燒也得起床煮飯給何寶榮;故意以藏著何寶榮的護照、囤積香菸的手段,企圖將他困住在二人的
關係中;但結果只是被不羈的「男方」一次又一次傷害。風流成性的何寶榮只會厭倦一成不變的枯燥關係,每每總是夜出鬼混尋求刺激、背叛忠誠的「女方」。《春
光乍洩》將這段關係異性戀化,令觀眾消除不安感,令電影足以成為一套主流電影;可惜的是,觀眾從片中吸收的仍是保守不實的意識形態,難以真正嘗試進入了解
同性戀者的世界。
電影的確沒有明言他們在戀愛關係上的心理性別,有評論認為,開首的性愛場面不單讓觀眾了解他們同志的身
份,更從他們性交的上下體位看出誰是這段關係中的「主權者」。然而我認為以此來作劃分的標準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憑日常的相處模式及總而觀之,這段關係實際
上的主權者其實是何寶榮,而不是在床上壓著對方的黎耀輝;加上同性戀人的「零」、「一」性角色可以經常轉換,又或可以同是兩者、有雙重身份,單以「性」來
斷言分析有欠公允。
何寶榮除了是負心漢,更加被描繪成性慾濫交的同性戀者,有著不同的男伴。而黎耀輝亦在被背叛的絕望之際,也重複施虐者何寶榮的行徑以尋安慰:在公廁、色情電影戲院尋找一刻歡愉的性伴侶。以下是他當時的獨白:
「我一直以為自己同何寶榮唔同,點知原來寂寞起上嚟,個個都一樣。」
「以前我一直都唔鐘意去公廁搵人,嫌污糟;但係近來都會去下,貪方便。」
將
同志的性觀念描述得如此開放,只重肉慾,是對他們嚴重的指控。同志往往被主流媒體以偏概全的塑造成濫交、虧欠道德,歧視了部分專一、追求精神交流而非性的
同性戀者。況且若將黎耀輝那句:「個個都一樣」解讀成不同性向的人,就顯示出媒體描寫社會將「性」了解成「寂寞時的消耗品」,一夜情被浪漫化、轉換成順手
拈來的溫柔﹣﹣這種將「性」與愛情、感性關係割裂,視為心靈空虛時的補充法,被催化得並無不妥。
故事一開始的背景,是一對同性戀人遠離香港的道德枷鎖,避走飄泊到「世界盡頭」阿根廷﹣﹣這個香港地理上的反面、以至主流意識倒轉的異鄉。黎耀輝的角色是典型香港同志、備受親人歧視和疏遠,對其父親感到愧疚和掙扎。
然
而,即使他們逃到阿根廷,也始終擺脫不了同性戀身份難以堂正展示的潛意識。整片中的氛圍總是陰沉昏暗,場景主要取自餐廳暗巷、擠迫黑漆的房間、公廁;即使
黎耀輝在大白天踢足球,都只能屈膝於環境昏黃欠公開的隱蔽小巷。這種環境的營造除了帶出這對同性戀人憂鬱神傷,更有他們怎逃也不見得光的意味。
黎耀輝在故事末段深受小張(張震)影響。他感言:
「我見到小張屋企人,終於明白佢點解可以咁開心,因為佢去幾遠都可以有個地方返轉頭;我唔知見到老竇會點,到時先算啦。」
小
張表現含蓄,沒被刻意描寫出性取向,但表現陽剛。小張曖昧地飾演著一個正氣活力的年輕救贖者,將沉淪被困性慾苦海中的同志﹣﹣黎耀輝拯救出來。這種收尾的
方式,雖然不是「拗直是同志唯一結局」的普遍處理方式,但小張將黎耀輝的情感釋放,令他重返香港、面對同性戀的現實、面對父親;卻是異曲同工地隱含著同性
戀者最終仍需被一個「正常人」救贖,依靠高一等的異性戀者,向他們學習借鏡;才可以回到正軌,得到啟示,落入傳統的思維模式。
加
上,第十七屆金像獎中奪得最佳男主角的,是梁朝偉而不是張國榮,兩者的演技同樣出眾,在此不多作比較;但很多人對梁朝偉較值掌聲的原因是,觀眾已將戲中人
何寶榮與張國榮劃上等號,張國榮只是做回自己,如當年頒獎典禮上曾志偉一句:「咁張國榮嗰啲係堅料嘛」,因同性戀性向而矮化他們的用功及成果。然而,梁朝
偉則是真男人忍辱負重地演一個與主流道德觀背道而馳的同性戀角色,這種由「正常人」演一個「不正常人」的為難及專業精神、甚至不惜與公言自己是雙性戀者的
張國榮演一場激情的床戲,就特別值得嘉許和欣賞。這種想法從根本上便病理化了同性戀者,又在潛意識上強化和確認了異性戀者的優越,從電影回到真實,社會始
終只擁護異性戀者。
今日,同性戀者在主流傳媒的塑造中依然存在偏見,但我認為電影作為一種藝術表現,難以規範它必定要為哪
些族群發聲辯護、要導演為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擱上責任。加上區區一套電影,我的疏散分析及主觀已見,又豈能作為剖析廣大同性戀者這些真實生活、切膚感受的標
準?不如讓我只大逆不道、膚淺靜心地欣賞一下《春光乍洩》的光影美景,陶醉在阿根廷異鄉悲戀當中……
參考文獻:
游靜,《性/別光影:香港電影中的性與性別文化研究》(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5)
洛楓,《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香港 :三聯書店 (香港)有限公司,2008)
潘國靈、李照興,《王家衛的映畫世界》(香港 :三聯書店 (香港)有限公司,2004)
電影雙週刊編輯,《張國榮的電影世界》(香港:電影雙周,2010)
2013年9月30日 星期一
生活在一個森林
我來自一個密林。
這裡的人不愛放鬆臉上任何一件肌肉,可以說是吝嗇於展示喜悅。
他們對身外物尤其注重及執著,被花花綠綠的符號擺弄得時時叫苦連天。
有一種興趣,
他們共同喜歡收集多餘的時間,他們都認為耐性是弱者的病癥。
有時候我也加入戰團
但很多時候,我都是迫不得已。
追趕著輸送帶的流浪者
病重的戰馬張口 嘔吐一堆早經急不及待、各就各位的
時間獵人。
他們的胸口都懸掛著一個個勳章:絲毫不差、飛快疾馳
從地底湧出的洪流推我冒出到另一個地洞
我不願成為他們的攔水閘,我甘願奉獻多餘的光陰使你可以稍息
可是你一手推開我
你覺得我是弱者
你覺得我未了解不斷向前衝的美德
我來自一個活的密林
心跳來自高跟鞋的哀鳴嚎叫
血脈是流動不息的軍隊兵馬
你在半路等我
紅黑紅紅黑
肉檔用鐵勾懸掛著待沽的肢體
紅燈罩下的鎢絲燈泡令凍肉看來更鮮活,是商學院也學不了的智慧
叫賣聲有種苦澀沙啞的人情味
主婦殺價、「搭條蔥」的口技與檔主日夜角力
竹簍與齊整疊好的菜蔬,兩方的映襯是歷久不衰的藝術品
街市是我城的瀕危物種,被追殺得奄奄一息;濕漉的地面在哭。
城裡偷閒
草在這個城市被受保護,比歷經數十載人情的建築更矜貴。能被合法擁抱的草地好像特別翠綠,可能因為腳底養活了他們本應被踐踏的自虐本性。大約一年前,我愛上了上環那片被高樓包圍的青蔥。
每逢假日,總有些住在火柴盒的人,幸運逃離大商場的魔掌,在一堆綠上面喘息天然流動的空氣。我在這裡吃的水果總是比較甜,也許因為某幾口觸破了小孩吹出的肥皂泡,因而產生了某種化學作用。我喜歡倚著小草午睡,與他們同步光合作用。草地上的人就是誤中小孩失誤的皮球,也面帶笑容;我一直覺得是卑微又驕傲的草教曉了城市人寬容。
我以為科技撕裂了人與人的關係,可是這家人卻被智能的相框拉近、合成一體。
拾芳者
蘭桂騰芳。煙圈朦朧了理性的香港島;來來往往的飲食男女、酒精浸泡的光管、節拍聲伴隨趕忙的火紅色。
威靈頓街的太陽只屬於西面,東面在夜裡被赤裸和高跟鞋佔領。攘往熙來選擇把不合群的人透明起來,例如默默收拾餘慶的步履和一頭頭無奈的白髮。
漫長的夜裡無人能夠阻塞擁抱陌生的單行路,無人願意破開拾芳的死巷。
訂閱:
文章 (Atom)